407期・Cover Story 軍工經濟篇
國防需求驅動 加速軍民合作科技創新
全球軍費攀升 地緣政治下的軍工經濟崛起
◎撰文/陳玉鳳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Brave1、AFWERX、Lockheed Martin、Rheinmetall

當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大幅升高,導致各國國防支出急遽增加,軍工產業鏈再度成為全球製造業與投資焦點。不同於過去由國防大國主導的軍備競賽,現代軍工經濟形態已明顯轉變,從單一武器製造擴展為結合科技創新、產業投資與就業支撐的綜合性經濟體。
烏俄戰爭未止、以哈衝突延燒、美中關係緊繃,加上台海情勢緊張,使各國國防預算持續攀升。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24年4月發布的報告,2023年全球軍事支出達到2.443兆美元,年增6.8%,為史上最高,並已連續第九年成長。美國以9,160億美元居首,占全球總額的37%;中國大陸排名第二,為2,960億美元,占12%;俄羅斯則以1,090億美元位居第三,占4.5%。
雖然SIPRI尚未公布完整2024年數據,但據各國政府與研究機構公開預算資訊,國防支出持續上升已成趨勢。美國2024財政年度國防預算約為8,414億美元;中國大陸2024年國防預算達2.45兆人民幣(約3,450億美元),官方宣稱年增幅為7.2%,不含隱性軍費的實際支出則可能更高。「隱性軍費」(off-budget military spending)指的是未列入國防預算官方公開數據,但實際與軍事活動有關的支出。俄羅斯2024年軍費則高達13.2兆盧布(約1,290億美元),占其聯邦預算逾30%。
戰場智慧化 新創成軍事供應新勢力
國防預算提升,不僅鞏固傳統軍工產業,也推動技術轉型。現代武器系統日益朝智慧化、自動化與數位化的方向發展技術。以烏克蘭為例,面對俄羅斯強大的電子戰能力,烏克蘭軍方與2023年4月啟動的國防科技創新平台Brave1合作,研發並測試以光纖控制的無人地面載具(Unmanned Ground Vehicles,UGVs),並計劃將光纖控制技術擴展至空中和海上無人載具,藉以提升在高干擾環境下的作戰效能。
英國國防部近年則積極投資於先進偽裝技術。這些技術的核心在於開發多光譜偽裝材料,能有效干擾敵方的多種感測器,包括可見光、紅外線和熱成像設備。其中,英國公司BCB International推出的「多光譜偽裝系統」(Multi-Spectral Camouflage,MSC)是一項突破性的技術。該系統利用先進材料,能吸收、反射或散射不同波長的輻射,進而在視覺、紅外線和熱成像等多個光譜範圍內有效隱藏軍事裝備。這種偽裝技術已被應用於烏克蘭戰場,幫助部隊在面對敵方無人機和先進監視系統時,降低被偵測的風險。
此外,英國國防部還與科技新創公司合作,開發專門針對AI系統的偽裝材料。例如,Advai公司正研發一種特殊的印刷材料,能迷惑敵方的AI識別系統,使其無法正確辨識軍事車輛。這項技術的目標是讓軍事裝備在敵方的自動化監控系統下變得「不可見」,進而提高部隊的隱蔽性和生存能力。
這些投資反映英國國防部對未來戰場技術的重視。根據英國國防部制定的「國防科學與技術策略」(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簡稱DST Strategy),未來4年將投入至少66億英鎊(約88億美元)於研究與發展,涵蓋先進材料、AI和自主系統等領域,以保持英國軍隊的技術優勢。
整體看來,軍民合作已成主流,軍工經濟不再僅依賴國有重工企業。美國國防部創立的國防創新單位DIU與空軍創新機構AFWERX,皆與矽谷新創企業合作開發AI、無人機、資安與量子技術。據布朗大學報告,2021至2023年間,創投資金投入國防科技新創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

軍民合作已成主流,不再僅依賴國有重工企業,美國國防創新單位DIU與空軍創新機構AFWERX,皆與矽谷新創企業進行國防相關合作。
面對亞太區域安全環境的急遽變化,日本政府亦大力推動國防現代化與軍工經濟布局,將科技創新視為核心戰略。從2023年起,日本啟動為期5年的國防現代化計畫,總投入金額達43兆日圓(約3,210億美元),目標是在2027年前將國防預算占GDP比重從傳統的1%上升至2%。
為強化自主防衛科技,日本於2023年設立「國防創新科技研究所」(DISTI),由防衛裝備廳(ATLA)主導,參考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模式運作。ATLA專責推動人工智慧、機器人技術、量子通訊、無人系統等具突破性潛力的軍用科技,並積極促成技術商品化與戰場應用的轉化。據報導,DISTI已與美國、歐洲研究機構建立合作機制,並吸納民間科技專才加入。這類「軍民融合」的新結構,也改變過去日本防衛科技長期封閉與保守的發展模式。
除中央研究機構外,日本民間企業也積極投入軍用應用的技術轉化。京都的Mitsufuji公司從可穿戴科技出發,轉向研發高導電性抗電磁干擾纖維,用於軍機與通訊裝備防護;東京的新創Innophys開發的外骨骼裝置已獲得自衛隊採用,以提升士兵長時間作業的機動性與安全性。防衛省亦透過技術徵案制度,邀請新創與中小企業參與國防專案,藉以拓展國內軍工產業供應鏈。
同時,日本也表態考慮加入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定(AUKUS)第二支柱(Pillar II),參與量子計算、無人載具、網路安全與AI等先進防衛科技的國際研發聯盟,進一步強化其在印太安全架構中的戰略角色。日本防衛省官員多次強調,未來的防衛競爭不只是「軍備競賽」,更是「科技能力與產業整合能力的比拚」。
德國工業重整 汽車產能轉向軍工製造
軍工經濟的另一項關鍵效應,是對地方就業與產業鏈帶來穩定貢獻。與其他高技術製造產業相比,軍工產業往往具有「高附加價值、長期訂單、產業鏈長且分工細密」等特性,能帶動中小企業升級並穩定地區經濟。例如,美國航空航太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主導的F-35戰機計畫,不僅是全球最龐大的戰機專案,也是涵蓋全球9國、橫跨美國45個州、超過1,500家供應商的龐大產業聯盟。根據官方資料,該計畫將在美國境內創造超過12萬個工作機會,並以「每售出一架戰機,就延伸美國10至15年工業活動」作為長期的宣傳主軸。

美國航空航太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主導F-35戰機計畫,是涵蓋全球9國、逾1,500家供應商的龐大戰機專案。
這些例子顯示,軍工經濟不再只是「大國防預算」與「大企業合同」的專利,而是具有明確就業外溢效益與中小企業參與機會的經濟體系。
對某些國家而言,軍事採購不僅是國安政策的延伸,更是國內產業升級、地方經濟振興與就業穩定的戰略工具,例如德國。根據優分析(UAnalyze)產業數據中心指出,德國長期仰賴汽車工業作為經濟支柱,但在電動車轉型不順、全球競爭激烈與需求放緩的多重壓力下,這個支柱正開始崩塌。像是工廠關閉、裁員潮不斷,讓這個製造大國面臨重整結構的難題。在此情況下,因地緣政治緊張與國防需求暴增而崛起的軍工產業,被視為極有可能取代汽車產業的新動能。
尤其軍工與汽車製造兩大產業間並非互斥,而是出現互補的可能。部分軍工企業開始承接汽車產業剩餘的產能與人力資源。例如,德國主要國防與汽車零組件製造商─萊茵金屬(Rheinmetall AG),計畫將柏林與諾伊斯的2座汽車零件工廠,轉型為生產軍用設備的據點,將併入其武器與彈藥部門,但保留部分汽車零件製造,採「混合工廠」模式,新工廠將專注防護設備與機械零件,以滿足全球國防訂單需求。
專注於軍事感測器技術與國防電子系統的德國領導企業亨索爾特(Hensoldt),則計畫從汽車零件供應商Bosch與Continental吸納約200名員工,擴大TRML-4D雷達系統的生產規模。而汽車零件製造商ZF Friedrichshafen也正評估轉入軍工領域,以對抗持續惡化的訂單與裁員壓力。

烏克蘭軍方攜手國防科技創新平台Brave1研發出無人地面載具,甚至計劃以光纖控制技術擴展空中及海上無人載具,提升作戰效能。
從經濟數據來看,這樣的產業轉型蘊藏潛在效益。根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Y)估算,若德國將國防支出提升至GDP的3%,預估能創造每年約255億歐元(約288.6億美元)的新增投資,進一步帶動420億歐元(約475.4億美元)的生產與服務活動,並新增約24.5萬個就業機會。這對德國當前低迷的經濟而言,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然而,即便前景看似亮眼,仍有隱憂。軍工產業的高度專業性使其無法完全承接汽車製造業的人力與技術,從內燃機技術轉入雷達系統、裝甲防護等領域,並非短期可實現的線性轉移,這樣的技術門檻可能成為汽車業轉型過程中的一大挑戰。
儘管如此,軍工產業正逐步成為德國製造業的新支柱。Rheinmetall公司於2022年納入德國DAX 30指數,目前市值已達約390億歐元(約441億美元),為川普當選前的2倍。2024年前9個月,其武器與彈藥部門營業利潤達3.39億歐元(約3,830萬美元),年增近100%;反觀汽車零件部門僅為7,400萬歐元(約8,370萬美元),還出現3.8%的下滑。Rheinmetall執行長阿明‧帕佩爾格在2025年2月於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隨著美國總統川普呼籲歐洲提高國防支出,歐洲面臨的安全壓力日益增加,「歐洲的安全局勢促使我們立即行動,公司成長速度將比預期更快。」
當汽車業正經歷去碳化與全球化逆風,德國「造車大國」身分或許正轉向「造坦克大國」。軍工業是否能穩定成為德國經濟的新引擎,仍有待政策穩定、國際形勢與產業韌性共同驗證,但至少從當前局勢來看,這場工業再平衡的實驗,已重新啟動。

德國國防與汽車零組件製造商Rheinmetall已逐步成為製造業新支柱,市值已達441億美元。
戰場AI科技進展 引爆倫理爭議
在全球軍工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不能輕忽科技武器的道德與法律爭議。特別是自動殺傷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LAWS)和軍用人工智慧(AI)的應用,引發國際社會對倫理、法律和人權的深刻討論。
自動殺傷系統是指能在沒有人類直接控制下,自主選擇和攻擊目標的武器系統。這類系統的發展,引發其是否符合國際人道法(IHL)的質疑,特別是在區分戰鬥人員和平民及攻擊的比例性方面。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持續呼籲禁止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系統,認為這些系統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並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然而,國際社會在如何規範法規仍有分歧。一些國家主張應完全禁止這類武器,而另一些國家則認為現有的國際法足以因應挑戰,這種分歧使得在聯合國《特定常規武器公約》框架下的談判進展緩慢。
人工智慧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日益廣泛,從情報分析到無人作戰系統,AI愈來愈重要。然而,這也帶來新的監管挑戰。歐盟於2024年通過《人工智慧法案》(AI Act),這是全球首個全面規範AI的法律框架,旨在確保AI的安全性和對基本權利的尊重。所謂基本權利,包含對人身自由與尊嚴、隱私與個資保護、非歧視原則、言論自由與法律救濟權等核心價值的保障。然而,該法案對軍事AI的監管相對薄弱,主要由各成員國自行負責,這引發對於跨國協調和監督的擔憂。
此外,AI在軍事決策中的應用也引發道德爭議。例如,以色列國防軍被指控在加薩地區使用名為「Lavender」的AI系統進行目標識別,該系統據稱在缺乏充分人類監督的情況下,將數萬人標記為目標,導致大量平民傷亡。這一事件凸顯在戰爭中依賴AI進行生死決策所帶來的風險。
綜合以上,軍工經濟的興起,絕非單純的軍備擴張,而是涵蓋供應鏈重構、科技轉向與國家政策調整的綜合性議題。從美國矽谷新創企業參與無人機、AI戰場管理系統,到日本企業將穿戴科技應用於軍用抗電磁材料,或德國以造車能量轉為軍備產能,每一項案例背後都是對國家戰略、企業彈性與科技整合能力的高度考驗。
然而,快速擴張的軍工經濟,也讓國際社會面臨愈來愈複雜的倫理與監管挑戰。簡言之,從軍費預算到就業轉型、從科技創新到倫理規範,軍工經濟已不再只是武器與裝備的製造,更是國家如何在地緣風險與科技浪潮中重新定位經濟動能的轉變。■
發行人語
轉危為機打造經濟新引擎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軍工經濟篇
全球軍費攀升地緣政治下的軍工
經濟崛起
Cover Story 重建篇
烏俄戰爭尚未結束重建商機蓄勢待發
Cover Story 台灣篇
提升自主國防實力帶動軍工產業新動能
|推薦閱讀|
特別企劃
寵物商機無窮從罐罐到智慧項圈
元宇宙爆發
數位轉型
從困境走向轉機以數位應用突破
新關稅障礙
企業領航
軒榮科技成功打造和牛品牌「滋賀一世」
亞太視角
美國「小額包裹關稅」引爆
跨境電商戰火升高
歐美非焦點
G20的非洲元年全球布局重心加速南進
產經情勢
關稅戰火延燒全球國際貿易進入動盪期
法律放大鏡
銷美產品原產地判斷風險
行銷實戰
社會創新三步驟提升品牌競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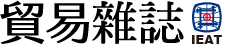
![30771_公會LOGO%20W%20[轉換] 01](img/30771_公會LOGO.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