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期・Cover Story 經濟篇
單一依賴漸遠 產業多元正起航
能源與地緣之變 全球經濟版圖的世紀轉型
◎撰文/鄒明珆 圖片來源/HYUNDAI、Shutterstock

從利雅德到杜拜,中東的天際線正展現國家在科技與經濟上的新布局。過去依賴石油的經濟體,正積極尋求多元化轉型,以應對全球油價波動、地緣政治變化與國際貿易新格局。這場轉型不僅涉及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反映出區域在能源、科技與資本運用上的長期規劃與戰略思考。
國際貨幣基金在2025年4月的報告中,以「在迷霧中開闢道路」形容當前的中東經濟格局。持續的油產削減、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與全球貿易格局的調整,正在削弱區域的成長動能。世界銀行的數據進一步揭示出不同節奏的發展: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憑藉非石油部門的韌性,2025年經濟成長率有望回升至3.2%;而區域內其他國家,如土耳其則仍面臨高通膨壓力(截至2025年7月,年通膨率為33.5%),加上沉重公共債務,構成雙重挑戰。
推動這場轉型的力量,不僅源自應對氣候變遷的長期承諾,更直接的壓力來自兩大挑戰:油價震盪對財政的衝擊,加上龐大青年人口帶來的就業需求——這些均非傳統油氣產業所能獨力承擔。沙烏地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PIF)坦言,為「低排放的未來」做好準備,是其轉型戰略的核心驅動力。
然而,改變並非一蹴可幾。根據世界銀行觀察,中東與北非(MENA)地區私營部門在資本投入、人力發展與創新方面表現疲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亦顯示,202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已連續第二年下降11%,且2025年前景依舊低迷。這表示,中東各國須在萎縮的全球資本中爭奪有限資源。
更關鍵的是,中東經濟正在沿著兩條不同路徑發展:海灣國家動用數千億美元主權財富,積極打造AI基礎設施與未來城市,企圖從根本上重新建立新的產業競爭優勢;土耳其則依靠既有地緣位置與工業基礎吸引資本,發揮現有優勢。這兩種模式——前者可稱為「資本創造」,後者可視為「優勢利用」——正成為新中東經濟格局的關鍵轉型座標。
Keyword|主權財富
國家成立的投資基金,主要資金來自石油收入、貿易順差或外匯儲備,目的是讓國家資產增值,同時支持長期經濟與戰略計畫。
沙國巨資布局 重塑經濟版圖
在分化的經濟版圖中,沙烏地阿拉伯成為最積極推動經濟重塑的代表。沙國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推進「2030願景」,試圖從石油巨擘轉型,打造製造與觀光的重要樞紐。
其核心推手「公共投資基金」(PIF)不僅被評為全球最具價值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品牌之一,資產管理規模2025年更突破1兆美元。在國內大手筆推動NEOM未來城、紅海全球(Red Sea Global)等關鍵投資,對外則精準投資Uber、Tesla等全球龍頭企業,引進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構築新興產業生態系。這場轉型伴隨著深度的財政與法規改革:非石油領域的政府收入已在2025年上半年達47%,並透過全新的統一《投資法》與外資房地產新政,為國際資本打開商機大門。
沙國的轉型不止於政策宣示,而是直指高科技與新產業鏈的核心環節。公共投資基金成立國家級AI公司Humain,並在2025年LEAP科技大會上敲定總額逾40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涵蓋Nvidia、AMD等晶片巨頭的GPU供應與數據中心投資。同時,與義大利輪胎製造商倍耐力(Pirelli)及韓國現代汽車的合資工廠正推動沙烏地阿拉伯本土製造業升級,使沙國成為區域製造新據點。
觀光與綠色能源則構成另一條成長曲線。2030年遊客目標已從1億人次上調至1.5億人次,紅海全球等奢華度假區的運營完全建立在再生能源基礎上。公共投資基金承諾向綠能投入194億美元,並主導全國70%的再生能源設施,目標在2030年達到50%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這些大型計畫間形成產業發展內循環:NEOM需要綠電、觀光項目則是催生航空與基礎建設、製造與物流則在供應鏈中同步受益。對投資者而言,這是一幅充滿希望的藍圖,儘管背後依然隱含高端人才缺口、地緣政治穩定性與項目執行難度等不少的現實考驗。

沙烏地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與現代汽車合資,正式舉行中東製造廠動工儀式,推動沙國汽車產業轉型、在地化製造與人才培育,呼應多元產業與高科技發展目標。
阿聯酋、卡達 主權AI雙路徑
相較於沙烏地阿拉伯從零開始的大規模轉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是在既有基礎上的「性能升級」。憑藉著成熟的金融與物流樞紐地位,阿聯酋正積極地向全球AI與高科技領域加速邁進。
阿聯酋的主權財富基金穆巴達拉投資公司(Mubadala)掌握3,300億美元資產,近5年的平均年收益率達10.1%,成為資本與科技結合的核心引擎。2024年,阿布達比成立國家級科技投資公司MGX,聯手穆巴達拉與本土科技巨頭公司G42,意圖整合國家AI資源並拓展國際合作。同年,微軟對G42投資15億美元,為阿聯酋吸引頂級戰略資本寫下關鍵里程碑。根據新創企業投資分析平台Tracxn統計,阿聯酋科技業在2025年上半年融資總額達10億美元,較2024年下半年激增133%,其中金融科技領域表現最為亮眼。
鄰國卡達則是以全球前三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國優勢提供國家產業轉型資金。主權財富基金卡達投資局(QIA)早在2020年便停止新增油氣投資,改以科技、媒體、電信、醫療與永續能源為核心發展方向;2024年投資1.8億美元於關鍵礦物公司TechMet,布局能源轉型所需的鋰、鈷等金屬資源;2025年初更啟動2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計畫,專注於再生能源與永續房地產,支持2030年前達成4GW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的目標。
兩國雖路徑不同,卻在「主權AI」(Sovereign AI)戰略上殊途同歸。從成立國家級龍頭企業、開發阿拉伯語大型語言模型,到掌握數據中心與雲端基礎設施,這不僅只是經濟布局,更是戰略自主與國家安全的體現。對於全球科技公司而言,與這些主權實體建立深度合作,已成為進入市場的門檻與捷徑。
在這場高科技與資本交織的競賽中,中東海灣雙國正以自己的語言,書寫未來的全球規則與秩序。

卡達以液化天然氣優勢提供轉型資金,近年聚焦科技、永續與能源轉型,投資關鍵礦物與綠色債券,推動2030年前再生能源目標。
土耳其 近岸製造新賽道
離開海灣地區,土耳其的路徑則更依賴地緣位置與產業基礎,形成與主權資本模式截然不同的發展邏輯。土耳其的轉型,像是在搖晃的鋼索上平衡前行:一端是地緣優勢帶來的機遇,另一端則是貨幣與債務壓力的現實。其核心策略是運用橫跨歐亞的絕佳地理位置,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浪潮中,承接來自歐洲的近岸外包(nearshoring)的製造訂單。
國際評級機構標普(S&P)在2025年4月維持土耳其的「BB-」評級,預測全年經濟成長2.7%,肯定緊縮貨幣政策的成效;但惠譽(Fitch)同時警告,里拉持續貶值與企業高額債務,將使工業企業的淨負債相對於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EBITDA)的比率在2025年升至3.8倍,增加信用風險。
即便如此,資本市場仍用行動投下信任票。2024年土耳其吸引113億美元外資,製造業占比高達34.5%,居各行業之首;2025年前5個月,外資流入同比再增加16%,達到47億美元,展現「近岸製造」的強大韌性與持續吸引力。
支撐這股能量的,是一波基礎設施的建設浪潮。根據土耳其國營的安納杜魯新聞社(Anadolu Agency)的報導,2025年上半年,土耳其建築業承接的國際項目金額達62億美元。其中,世界銀行於8月核准的7.08億美元貸款,將用於升級全國電網,為2035年前實現120GW風能與太陽能裝機容量奠定基礎。政府的《2025年投資行動計畫》更將綠色能源、數位經濟與氫能戰略列為優先項目。
土耳其的轉型模式依託其獨特地緣優勢,借助國際金融機構與戰略夥伴的資金與信用背書,為能源與基礎建設轉型提供穩健支撐。這種外部資本的加持,不僅有助緩解國內整體經濟挑戰,也讓土耳其在全球供應鏈重組浪潮中,占據重要地位。

土耳其加速綠能轉型,政府與國際合作推動風能與其他相關永續能源開發,打造清潔能源基礎設施。
高科技重塑供應版圖 台灣迎接中東新契機
中東的經濟版圖正同步沿著兩條軸線快速轉型:一方面,海灣國家挾著主權基金之勢推動國家級產業革命,從石油經濟轉向AI與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另一方面,土耳其則是借重其地緣樞紐地位,打造兼具自主性與韌性的產業模型。這場變局不僅重塑了中東自身的發展方向,也為全球供應鏈開啟嶄新格局。「中東走廊」逐步形成涵蓋先進製造(沙烏地、土耳其)、AI研發(阿聯酋)與綠能投資(全區域)的多元產業集群 與合作網絡,成為傳統東亞供應鏈外的關鍵替代節點,也將成為連接歐亞的戰略性新引擎。
資金流向與技術布局的變化,正在讓中東主權基金從過去的財務型投資者,轉型為全球高科技領域的「塑形者」。其在AI、半導體、綠能等領域的高額部署,使其成為全球創新企業無法忽視的合作對象。而這波浪潮下,台灣的角色也正在重組。過去以能源進口為主的經貿往來,正轉向更深層的技術共生。2024年台灣對中東出口總額成長達9.8%,顯示轉型的契機已悄然浮現。借鏡NVIDIA等國際企業的全球部署策略,台灣可結合核心研發與製造優勢,與中東資本與市場資源互補,在AI、資料中心等領域建立長期合作架構。
然而,中東市場的機會與風險始終並行。台積電對於阿聯酋建廠傳聞的低調回應,正反映出台灣企業在開拓新興市場時,須審慎拿捏地緣政治平衡。一方面是美國的國安聯盟與技術規範壓力,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大陸持續透過「一帶一路」滲透中東基礎建設與科技布局。台灣要在這張棋盤上站穩,不僅仰賴供應鏈韌性與技術實力,更需展現與西方生態系的深度兼容,並靈活應對各方戰略期待。
放眼未來,中東不再只是石油輸出地,而是全球高科技與供應鏈布局的重要節點。對台灣與全球企業而言,這是一條尚未飽和的成長曲線,同時也是一個重新嵌入新經濟體系、搶占全球戰略位置的歷史契機。在主權AI、深科技競逐加劇的時代,唯有將技術、資本與戰略判斷精準結合,方能在下一輪全球秩序重組中取得先機。■
發行人語
挑戰與機會並存的台灣貿易新篇章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總論篇
變局中東戰火、能源與AI賽局
的交錯未來
Cover Story 經濟篇
能源與地緣之變全球經濟版圖的世紀轉型
Cover Story 科技篇
算力新霸權崛起中東國家重塑秩序
|推薦閱讀|
特別企劃
全球變局下的經貿與人才戰略
特別企劃
AI驅動貿易革新人才培育開創未來
特別企劃
全球淨零推動轉型綠色技能重塑貿易業
特別企劃
強化經貿連結開拓台美合作新格局
企業領航
美杉工業聚焦利基市場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亞太視角
川普新關稅生效改寫全球貿易潛規則
國貿心法
進出口通關實務稅則稅率概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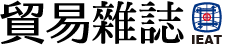
![30771_公會LOGO%20W%20[轉換] 01](img/30771_公會LOGO.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