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3期・Cover Story 總論篇
國際資本體系再造
新數位交易時代 重塑全球格局
◎撰文/鄒明珆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路透社

全球貿易支付正迎來一場由技術創新與貨幣主權競逐共同推動的重大變局。央行數位貨幣(CBDC)、穩定幣與區域清算機制的崛起,正重塑跨境資金流通規則。這股「數位貨幣浪潮」不僅挑戰長期依賴美元與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體系的結算秩序,也正重繪全球金融權力版圖。誰能率先掌握新世代金融基礎設施,誰就可能在下一輪經貿秩序中取得制度主導權。
自1973年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後,美元長期穩坐全球貿易結算核心。這套體系建立在兩大基礎:以美元為中心的單一結算貨幣體系,以及以SWIFT為中樞的跨境支付網絡。前者讓美國能掌握全球資金流向;後者則以標準化的金融訊息格式,成為國際銀行共通語言。
然而,這套高效體系也藏有結構性風險。SWIFT雖非直接轉移資金的機構,卻握有金融資訊的「閘門權」。一旦被排除於系統外,等同喪失全球金融通道。伊朗與俄羅斯等國皆曾因政治衝突而遭金融孤立,使各國認知到支付體系的「武器化」風險。各國開始反思:若金融基礎設施綁定單一國家利益,主權與經貿自主性將無從談起。
正因如此,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出現被視為重構國際清算秩序的契機。當區塊鏈技術與主權貨幣結合,跨境結算有機會擺脫代理行層層轉接的限制,達到即時、低成本且可追溯的交易模式。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全球已有逾百個經濟體投入研發,其中三分之一已進入實驗或試點階段。一場以技術為槓桿、以金融主權為核心的全球競逐正全面展開。
Keyword|布列敦森林體系
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金融制度,旨在穩定匯率與促進貿易,以美元為核心、黃金為後盾。
央行數位貨幣的雙極競賽 攻勢與防禦的戰略分歧
央行數位貨幣作為中央銀行直接負債的數位形式,因不存在信用與流動性風險,被視為最安全的數位資產。當前全球格局逐漸形成兩大陣營,以中國大陸為首的「攻勢型」體系及以美、歐為核心的「防禦型」體系。
中國大陸的攻勢戰略 數位人民幣的系統性挑戰
中國大陸以國家力量驅動數位人民幣(e-CNY),在技術進度與試點規模上領先全球。在其國內,e-CNY的核心任務是鞏固中央銀行在支付體系的主導權,對抗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等私人科技平台的市場壟斷。其兩層式營運架構,由人民銀行控制發行,商業銀行負責流通,確保央行的監管主權不被稀釋。
在國際層面,e-CNY被視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與挑戰美元霸權的關鍵工具。藉由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低成本結算方案,中國大陸正構築以人民幣為核心的跨境支付網絡。其終極目標之一,是建立獨立於SWIFT外的替代方案,降低在面對美國金融制裁時的脆弱性。
西方陣營的防禦與演進 鞏固現有體系的韌性調整
相較之下,西方經濟體採取更謹慎的防禦策略,重點在現代化並鞏固既有金融體系。歐盟的數位歐元被定位為「戰略自主」的象徵,目標降低對非歐洲支付網絡的依賴,並維持隱私與法治。歐洲央行強調,數位歐元將作為實體現金的補充而非替代。
美國則面臨更複雜的內部掣肘,零售型CBDC推進受阻。然而,華府的戰略焦點始終是維持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當公共零售CBDC難以推進,美元穩定幣(如USDC、USDT)反而成為實際上的「民間數位美元」。隨著監管框架推進,穩定幣被納入銀行體系監管,形成「批發優先、零售私營」的混合策略。
數位人民幣區域試點 建平行清算體系
在全球央行競相部署CBDC的版圖中,中國大陸的戰略布局最具體。若前一階段揭示了挑戰美元體系的意圖,接下來的行動則是如何將戰略具體化,透過跨境試點建立可運行的「平行清算體系」。
批發層面|mBridge多邊支付橋的戰略實驗
「多邊央行數位貨幣橋」(Project mBridge,mBridge)是中國大陸最具戰略意涵的布局。該項目由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國與阿聯酋中央銀行共同推動,並由國際清算銀行(BIS)創新中心協調。2024年中,沙烏地阿拉伯加入,覆蓋範圍橫跨亞洲與中東主要能源經濟體。mBridge以分散式帳本技術(DLT)為基礎,將跨境結算時間從數日縮短至數秒。
這項平台的戰略價值遠超技術層面。mBridge被視為「金磚支付」(BRICS Pay)的技術基礎,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可在SWIFT系統之外獨立運作的清算網絡。該平台是設計來支持多種央行數位貨幣,使非西方經濟體能以更低成本、去中介化的方式結算。若此模式成熟,將形成以多種主權數位貨幣組成的平行支付體系,對現有全球清算架構產生結構性衝擊。

因俄羅斯發動戰爭,國際支付系統展現「武器化」特性,使俄羅斯金融通道受限。
Keyword|分散式帳本技術(DLT)
一種讓交易紀錄分散存放、同步更新的技術,不靠單一中央機構就能保持安全與透明。
Keyword|金磚支付(BRICS Pay)
由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大陸、南非)推動的跨境數位支付系統,用意在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結算和金融合作。
Keyword|全球清算架構
跨國金融交易資金結算的制度與網絡,確保各國之間的支付安全、迅速與可追溯。
零售層面|香港沙盒與制度互通的試驗場
在零售應用層面,香港扮演數位人民幣跨境測試的關鍵節點。香港居民現可僅憑本地手機號碼開立e-CNY錢包,無需中國大陸內地的銀行帳戶。更重要的是,該試點實現了e-CNY與香港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FPS)之間的雙向連接,成為全球首個實際落地的CBDC-FPS互通案例。
這座「金融沙盒」讓中國大陸能在受控環境中調整CBDC的跨境操作機制,同時觀察外部市場對e-CNY的接受度。其成效將直接影響未來數位人民幣能否在更多區域金融中心擴張。
Keyword|沙盒(Sandbox)
指的是一種受監管機構允許、可進行創新金融服務或產品測試的安全實驗環境。
戰略應用|從能源結算到海外清算網絡
中國大陸也在基礎設施與能源領域推進數位人民幣結算。中國銀行萬象分行已被指定為寮國的數位人民幣清算行,成為數位人民幣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正式金融基礎設施;同時,數位人民幣也已應用於中國大陸與阿聯酋之間的石油交易。這些案例顯示,中國大陸正以務實方式推動人民幣計價體系滲透至戰略性貿易領域。
去SWIFT化的道路 金融體系邁向碎片化
隨著CBDC與替代性清算系統的興起,「去SWIFT化」正成為全球金融秩序重組的關鍵議題。這不僅是技術革命,更是一場關乎金融主權與制度支配權的博弈。
自1973年成立以來,SWIFT一直是全球跨境金融訊息傳遞的中樞。它提供一套高標準、安全且標準化的金融語言,使全球銀行能以統一格式溝通。然而,SWIFT的中立形象正逐漸式微。由於其總部位於比利時並受歐盟監管,必須遵守歐美制裁規範,導致其成為西方國家施壓與制裁的延伸工具。對許多新興經濟體而言,掌握自主清算系統不僅關乎效率,更是確保金融安全與主權自主的重要防線。

歐盟推動數位歐元,希望在現代化並鞏固金融體系下,降低對非歐洲支付網絡的依賴,同時維持隱私與法治保障。
中國大陸CIPS的防禦與共生
中國大陸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是最具戰略深度的替代方案之一。與僅傳遞訊息的SWIFT不同,CIPS結合支付、清算與結算功能,採用「實時全額結算」(RTGS)模式。
外界常將其視為SWIFT的替代者,但CIPS目前仍與SWIFT維持「競合共生」關係——超過80%跨境訊息仍透過SWIFT傳輸。CIPS採用與SWIFT相容的ISO 20022標準,兼顧穩定與擴張。從戰略角度來看,CIPS更像是一項「防禦型基礎設施」,用以強化中國大陸面對潛在制裁時的金融韌性。
俄羅斯SPFS與金融堡壘
俄羅斯的金融訊息傳輸系統(SPFS)則是戰略壓力下的「防禦堡壘」。自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俄羅斯為避免被切斷國際結算通道而自主開發SPFS,確保在制裁環境下仍能維持國內金融穩定。
目前俄羅斯正推動SPFS與CIPS的系統對接,試圖構築一個繞開西方制裁的獨立金融圈。然而,美國財政部已明確警告,任何新加入SPFS的外國金融機構都可能面臨二級制裁風險。這種「制裁與反制裁」的拉鋸,全球金融體系也正沿著地緣政治的界線出現日益明顯的分歧。
從SWIFT被視為制裁工具,到中國大陸CIPS系統的防禦布局,再到俄羅斯SPFS的獨立路線,全球金融體系正走向多極化發展,各系統間的互通性也愈來愈低。這種趨勢將使跨境資金流動更具政治屬性,也讓國際貿易結算的效率與穩定性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新型清算架構的兩條道路 mBridge與Agorá的對決
各國央行正尋求重塑跨境清算體系的制度方案。這場競賽最終集中於兩個項目的對決——中國大陸主導的mBridge與西方陣營主導的「阿哥拉計畫」(Agorá)。它們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哲學:革命性重構,或演進式升級。
mBridge以分散式帳本技術為基礎,建立一個由多國央行直接參與的單一平台——mBridge Ledger。該項目在2024年中已達「最小可行產品」階段,跨境交易時間可從數日縮短至數秒,展現取代傳統代理行體系的潛力。其戰略意圖極為明確:打造一個可獨立於美元與SWIFT之外運作的平行清算網絡。
相對地, Agorá 採取「演進式整合」策略。該計畫同樣由國際清算銀行(BIS)主導,成員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及歐元區等主要西方經濟體。其技術框架基於「統一帳本」概念,將央行貨幣、商業銀行存款及代幣化資產整合於單一平台,保留現有兩層式銀行結構的同時,實現數位化升級。與mBridge不同,Agorá並不尋求取代現行金融秩序,而是透過技術現代化鞏固美元體系的主導地位。
這兩個項目的差異,不僅是技術選擇的分歧,更反映出地緣政治的深層對立——一方追求制度替代,一方力圖維繫秩序。前者的終極目標是建立「非西方中心」的多邊結算體系;後者則致力於確保西方金融規範在數位時代的延續。
Keyword||實時全額結算(RTGS, 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一種銀行間資金即時轉帳與結算系統,交易在發生時立即、逐筆完成清算與付款,不需等待批次處理。
Keyword||「阿哥拉計畫(Project Agorá)」
由國際清算銀行(BIS)與多國央行合作推動的跨境批發型數位貨幣實驗。計畫透過分散式帳本技術(DLT),測試央行間能否以數位貨幣直接進行跨境結算,以提升效率、安全性與透明度。
區域支付機制 務實與自主的第三條路
當大國圍繞制度主導權展開競逐,新興市場國家則以更務實的方式推動金融自主化,藉由區域性清算機制實現「去美元化」與跨境效率提升。
非洲的「泛非支付與結算系統」(PAPSS),是由非洲進出口銀行推動的集中化基礎設施,目標在每年為非洲內部貿易節省約50億美元的交易成本。過去,非洲內部交易長期依賴美元結算,如今PAPSS讓企業能夠以本地貨幣完成支付,因此成為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的金融支柱,也是當前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去美元化實驗。
東南亞的「東盟支付連接」(APC)採取去中心化架構,透過串聯各成員國既有的快速支付系統,形成跨國互通的網絡。例如,馬來西亞旅客可在柬埔寨使用本地銀行App,以即時匯率完成支付,無需美元中介。這種輕量化整合,正促進東協區域貨幣在零售交易中的直接流通。
相較之下,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AEU)路徑則更具戰略性。其金融核心由SPFS系統支撐,明確服務於制裁環境下的金融自保需求。該聯盟正評估以CBDC作為未來跨境結算基礎,試圖在地緣政治分裂中建立「安全優先」的經濟網絡。
三條區域路線分別體現不同戰略:非洲與亞太重視效率與互聯,歐亞聯盟則著眼於主權與風險防禦。與此同時,mBridge與Agorá在制度層面競逐主導權,使全球清算體系不再由單一系統主導,而是出現多個區域與機制並行運作的新樣貌。
數位貨幣重構貿易金融秩序 新規則時代的臨界點
數位貨幣的興起,不僅是技術革命,更象徵全球經貿權力的再分配。從CBDC實驗到跨境清算重組,世界正逐步脫離單一貨幣的依賴,走向多中心、跨網絡的新格局。核心競爭不在誰發行更多數位貨幣,而在誰能建立更被信任的制度與基礎設施。
對企業而言,跨境支付正從靜態流程轉為動態互動。交易更快、更透明,卻也更複雜;金融效率提升的同時,規範與主權的界線被重新定義。如何在分散化環境中維持信任與穩定,將是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的新命題。
未來的國際貿易不再以美元或SWIFT為中心,而將在多元數位貨幣與區域網絡間運作。這是一個尚未定型的秩序,也是一場制度與信任的持久戰。誰能率先建立互信與互通的新型結算體系,誰就將掌握下一個世代的貿易金融主導權。■

因應金磚國家峰會,「金磚支付」(BRICS Pay)正透過mBridge平台構建獨立於 SWIFT 的數位貨幣清算網絡,挑戰美元主導的全球支付體系。
發行人語
數位貨幣啟動貿易新紀元
名家觀點
當年輕人「一言不合就離職」
主管必學六大技巧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總論篇
新數位交易時代重塑全球格局
Cover Story 應用篇
企業跨境轉型改寫商業運作邏輯
Cover Story 台灣篇
台灣數位支付策略監理突破與產業實踐
|推薦閱讀|
特別企劃
最糟的失眠時代!翻轉「睡眠負債」變商機
企業領航
元家企業冷凍水產品牌持續創造競爭力
數位轉型
AI驅動產業升級台灣企業鏈結全球新動能
電商加速器
智能轉型引領美妝產業升級
行銷與顧客互動重塑
亞太視角
地緣風暴來襲!企業的資本避險穩定器
產經情勢
液化天然氣供應擴張重塑世界能源版圖
行銷實戰
品牌圖像化讓價值看得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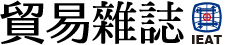
![30771_公會LOGO%20W%20[轉換] 01](img/30771_公會LOGO.png)
